
《可以阅读的图像》,[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孙淼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380页,108.00元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作家、编辑、译者、文学评论家、图书馆长,以及狂热的阅读者。这位曾出版过《阅读的历史》(A History of Reading)、《夜晚的图书馆》(The Library at Night)、《虚构地点词典》(The Dictionary of Imaginary Places)等诸多畅销书的作家,最终将阅读的热情与思辨延伸至了图像世界。2002年,英文版《可以阅读的图像》(Reading Pictures: What We Think About When We Look at Art)首次由兰登书屋出版。“曼古埃尔以他迷人的冷静、不慌不忙的方式,迫使你重新审视自己对艺术的遐想和信念”——《星期日电讯报》如是评价。而作者表示“这本书的诞生,源于让像我这样的普通观者能够阅读这些图像和故事的责任和权利”(前言,第I页)。因此,稍作浏览,读者就会发现,与其将它的类型归为“图像志”,毋宁说这是一本剔除了晦涩图像理论,打破艺术史线性叙事,将图像归还于“讲故事”的文化读物。
阅读的游荡者,游荡的写作者
曼古埃尔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随意的、有好奇心的旅行者(traveler):“我喜欢在漫无目的地游荡中探索那些可能看到的图像:风景、建筑、明信片、纪念碑和画廊等各种保存着当地记忆的地方。”(前言,第I页)这样的描述不禁令人联想起另一位沉醉于文字与图像的诗人波德莱尔,这位以笔调阴郁、观察冷峻著称的诗人,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沉着地漫步穿梭于城市,漫无目的地闲逛,却又暗暗地高度警觉的“游荡者”(flâneur)意象([英]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33页)。不同于波德莱尔聚焦勃兴于十九世纪的大都市及市民,曼古埃尔借助二十世纪以来愈加便利的交通与丰富的知识生产,将自己的“游荡”延展至更加辽阔的地理空间,将他那“不知餍足”的激情倾泻于对古今文明的观察与审视。
1948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曼古埃尔,由于父亲曾为阿根廷首任驻以色列大使的缘故,在特拉维夫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当七岁的小阿尔维托返回故乡时,已熟练掌握了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三门语言,这不仅为他日后以广泛而深刻著称的写作与翻译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他在成年后虽客居异国,依然能够从容融入当地生活,积极参与不同语境下的智识讨论。如果说童年的多语言经历丰富了曼古埃尔的阅读积淀,那么青年时期与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往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写作志向。
十六岁的曼古埃尔,课余时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格马利翁书店打工,偶然的邂逅,让他开始为失明了的博尔赫斯朗读书籍。这段关系从1964持续到1968年,而朗读间隙的交流,曼古埃尔称之为“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展现着它蕴藏的无穷宝藏”。在这三年中,二人在无数个午后时光构建的书籍世界,让这位年轻人时常觉得那就是他的生活世界([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和博尔赫斯在一起》,李卓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7页)。彼时,曼古埃尔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学院,因该校隶属大学,他有幸接受多位杰出大学教授的指导。如果不是后来阿根廷愈演愈烈的右翼恐怖活动,也许曼古埃尔会像他的前辈一样,在这片拉美热土上开启自己的作家生涯。然而,最终他还是不得已在1969年初离开故国前往欧洲,再一次开启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旅程,写作也成为曼古埃尔的“忒休斯之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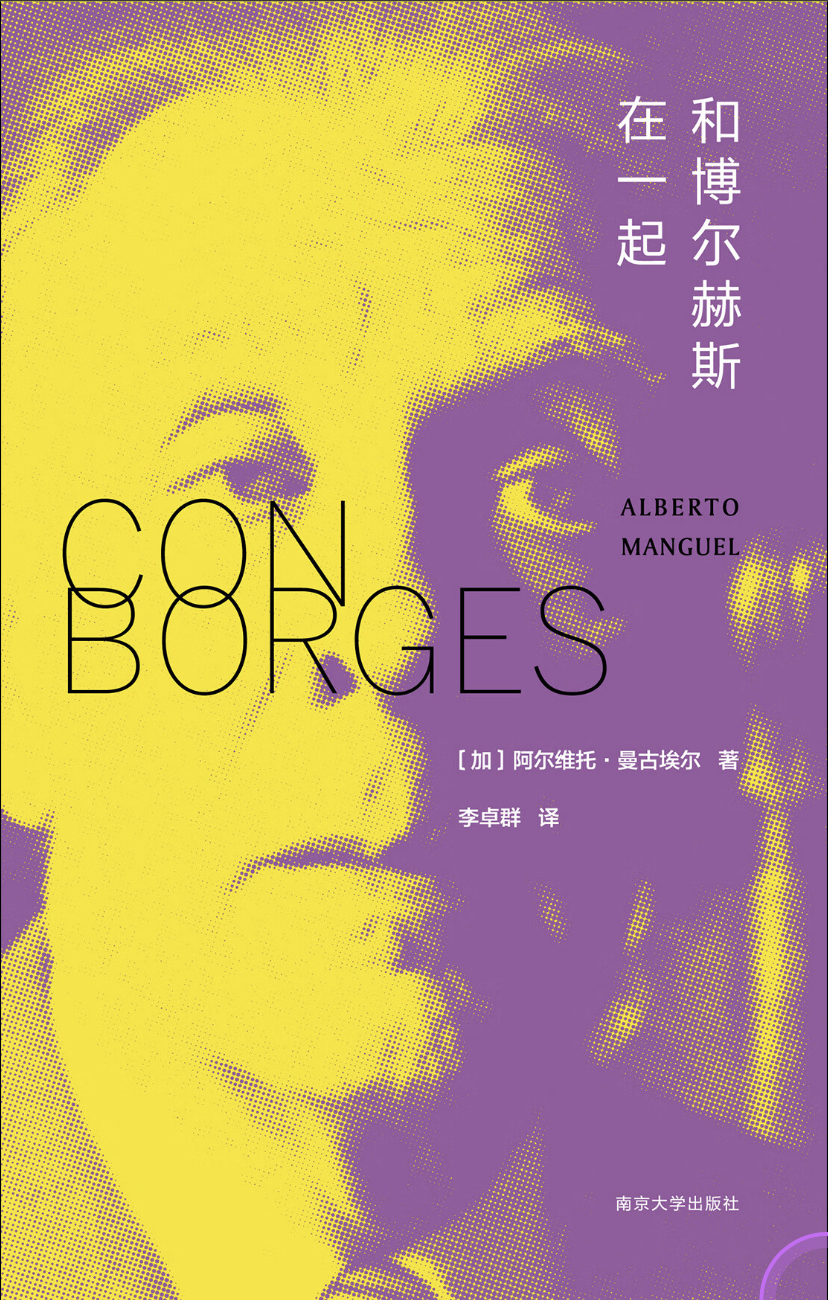
曼古埃尔著《和博尔赫斯在一起》
全球的旅居生活使曼古埃尔成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多年来他辗转于渥太华、里斯本、巴黎、纽约等地,行穿于文明交汇的都市,也徜徉在图文交织的时空之中。曼古埃尔的作品充满了跨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他的写作不仅探讨了文学、艺术与文化的关系,还通过个人经历,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在《可以阅读的图像》中,作者的博闻强识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充满了妙趣横生的比喻,通达有节的引用,柏拉图穴壁中摇曳的影子,苏美尔人眼中的鸟兽脚印,古希腊天文学家俯仰之间的星座神话,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自然隐喻,卡尔维诺笔下行者的塔罗故事,中国圣人杯盏里的茶叶形状,丁尼生诗句里的墙缝生花,复活节岛等待破解的传说,等等,都可以成为曼古埃尔向读者破译图像秘密的媒介。
艺术史缝隙的阅读
我们习惯于为历史上每一位艺术家、每一件艺术品在时间长廊里标注点位,仿佛非经由艺术史学家定夺后的创作时间、风格流派、社会背景等信息,观者才能获得对图像理解的安全感,才能坚定本是主观而发的审美向度。但在曼古埃尔的眼中,对图像的探寻只是出于艺术对他个人的吸引力。因此,在《可以阅读的图像》中,作者拒绝了传统史学的“系统性的阅读图片方法”,也不在乎艺术家的知名度,只选取浩瀚艺术史中那些让他魂牵梦绕、浮想联翩的图像。
该书共有十二个章节,以独立叙事的方式分别探讨了图像作为“故事”“缺位”“谜语”“见证”“理解”“噩梦”“反射”“暴力”“颠覆”“哲学”“记忆”和“戏剧”的不同主题。从巴洛克时期的巴西到十五世纪的佛兰德斯,从庞贝的伊苏斯战役马赛克拼贴到柏林大屠杀纪念馆,从绘画、雕塑、建筑到摄影,不管是抽象画、圣象画还是纪念碑,曼古埃尔都能利用他广博的学识游走于艺术、文学、神话之间,让原本静止的图像,在读者的脑中变幻出一系列新的意象。
整本著作中,除了首篇,其余十一个单元均使用艺术家的名字来命题。打开目录,读者可能会错愕,除了毕加索和卡拉瓦乔,其余的名字(琼·米切尔、罗伯特·康平、蒂娜·莫多提、拉维尼亚·丰塔纳、玛丽安娜·加特纳、菲罗塞奴、克劳德·勒杜、彼得·艾森曼)对于非专业的读者稍显陌生,这让我们再一次对作者提到的“个人吸引力”有了直观的感受。在艺术史中游荡的曼古埃尔,无意为成功者讲故事,更不屑书写艺术史中的胜利者,他不仅要为普通人争取阅读图像的权利,也要向“普通艺术家”归还讲故事的权利。
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断言,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德]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0页),但在图像爆炸的二十一世纪,新的故事反而借由现代媒介不断涌现。图像在传播中被反复“阅读”,任何一位有心人都可以赋予图像开口的可能性。格林·伯格说,“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英]格林·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曼古埃尔则更进一步强调观者的个体经验对图像理解的重要性。因此,他所讲述的故事常常也融合了对自我形象的反思与幻想。在这个层面上,他对是否“存在一种条理清晰的系统化图像阅读方式”的质疑不无道理(18页)。系统化的思维一旦被打破,那些沉寂在历史缝隙、社会边缘的图像便一涌而出。
图像、文字与情感
曼古埃尔提到,在开始撰写本书时,他的初衷是探讨人们的情感,即“情感是如何影响人们的阅读与艺术作品,以及情感如何受到二者影响的”(前言,第IV页)。但当他完成后,发现最终的成果与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然而,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他选取图像的动机、叙述的铺陈以及讨论的角度,完全植根于他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情感理解。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将图像带给他的微妙心理感受传递给读者,从而激发出类似的情感波动——不安、困惑、喜悦、恐惧、惊叹、悲悯与愤慨等情绪纷至沓来。
在“琼·米切尔:图像即缺位”一章中,曼古埃尔借由这位女性艺术家的大幅双联油画《两架钢琴》,探讨了图像的“不可见”。当作者第一次面对这幅抽象表现主义作品时,立刻被米切尔“暴雨般”倾泻的黄色和紫色笔触所震撼,感受到那“肆意挥洒的色彩、满溢的光明和自由狂喜中洋溢的幸福”(21页)。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作品中抒情与沉默之间的悖论性张力。当然,曼古埃尔并未止步于情感的震慑,而是通过文字进一步探寻,试图还原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下,如何阅读《两架钢琴》的故事。从美国现代艺术家波洛克的直觉感受式创作,到二十世纪初巴黎盛行的“自动写作”,从拜占庭的偶像破坏运动,到贝克特的虚无主义表达,曼古埃尔阐明了图像的“缺位”(absence)如何在观者的阅读过程中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

琼·米切尔绘《两架钢琴》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黄剑波等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解释道,文化和宗教通常会拒绝那些不纯的、混合的、边缘化的事物,因为它们无法被归类。而曼古埃尔,一个在历史的缝隙与边缘的“游荡者”,却总是被混合体和异常现象所吸引。在“图像即理解”一章中,曼古埃尔引导读者关注一位常常被艺术史研究者忽略或轻描淡写的女性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拉维尼亚·丰塔纳。她的作品,尤其是《托尼娜肖像》系列,令曼古埃尔深深着迷。托尼娜和她的父亲、弟弟因基因问题,全身布满毛发,外貌酷似“狼人”或“猫人”,因此,他们一家人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当时欧洲贵族的“怪物”画册里,并在宫廷中被当作类似侏儒的娱乐对象。围绕油画中的托尼娜形象,曼古埃尔阐述了丰塔纳在描绘这位少女及其家人时所展现的同情与尊重。通过她生动的笔法,丰塔纳将托尼娜那倔强、警觉且不苟言笑的目光永远定格在画布上。

拉维尼亚·丰塔纳绘肖像画
在描绘玛丽安娜·加特纳的篇章中,曼古埃尔对边缘性和混杂性的兴趣得以延续。“噩梦”系列代表了加特纳的典型风格,艺术家从老照片中汲取灵感,使这些充满“私人模糊”的画作弥漫着一种“美丽与邪恶”结合的怪诞美学。《恶魔婴儿》呈现了一个裸体婴孩坐在花卉纹样的圆形靠垫上,头上长着弯曲的公羊角,身上布满了骷髅和恶魔的纹身,与他纯洁的面容形成了强烈反差;另一幅《钢索上的克拉拉》中,一个穿着得体的小女孩提起裙边站在钢索上,脚下空空,而两具对视的骷髅分别咬住钢索的两端。这些图像糅合了摄影般的写实主义与强烈的幻想色彩,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梦境。加特纳的想象不断游移于“噩梦”与“神话”之间,既引发观者的好奇与不安,也为图像的阅读与解说带来了挑战。

玛丽安娜·加特纳绘《恶魔婴儿》
在“巴勃罗·毕加索”一章中,曼古埃尔展现了他对这位艺术家的保留态度。通过毕加索的创作,作者探讨了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让他好奇,又令他困惑。在曼古埃尔的理解中,艺术家和其作品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即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不应创作出具有道德感的伟大作品。但是,毕加索的存在和成功挑战了这一认知。毕加索曾自负地说道,“其他人对我来说并不是真的很重要,在我看来,他们就像阳光漂浮的小灰尘”,然而,他正是利用这些“小灰尘”创作出众多具有普世价值的画作(200页)。曼古埃尔通过还原《哭泣的女人》和《格尔尼卡》这两幅作品的创作过程,揭示了毕加索的另一面:他对情人施以暴虐态度,情感上予以践踏,将自己施虐所带来的痛苦形象转化为艺术中的公共哀悼对象。与此同时,曼古埃尔也试图解释艺术史上类似的悖论:一件艺术品如何将令人憎恨的行为(或爱的行为)转化为表达相反感情的符号,而这种新的符号又如何成为时代的语汇。

毕加索绘《哭泣的女人》
结语
曼古埃尔谦逊地将这本书描述为“杂乱的笔记和无名之文”(306页),然而,在他试图理解和解读这些图像的过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他不断追问的一些基本问题:艺术中的“真实性”是什么?艺术家的意图与作品的意义之间存在哪些关系?一个通过故意施暴而产生的艺术形象,如何能够成为对暴力本身的有力谴责?当然,曼古埃尔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他只是反复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问题,并对既有的公认结论表达质疑。
“当我们尝试阅读和解读油画的时候,它在我们眼中可能就像是坠入了误读的混沌一般,或者如同一片混沌中的多重解读。”(14页)曼古埃尔在本书中所做的,正是从这些深渊中打捞出更多关于图像的故事,同时又为这些故事的多重版本提供更广阔的开放性。他坦率地承认,由于个人视野的局限性,书中可能存在的遗漏与不足,这既是一位文化从业者对知识的谦卑姿态,也体现了他对不同语境下艺术观点的包容态度。虽然这本书写于二十一世纪初,但在当下这样一个看似交融与共,实则充满了文化与身份隔阂的全球化语境中,它依旧具有深刻的警醒与启示意义——无论你的教育、性别、民族、信仰甚至政治背景如何,当你面对一幅图像时,只要它让你驻足、凝视,引发片刻的遐想,你就有权利去阅读它,去讲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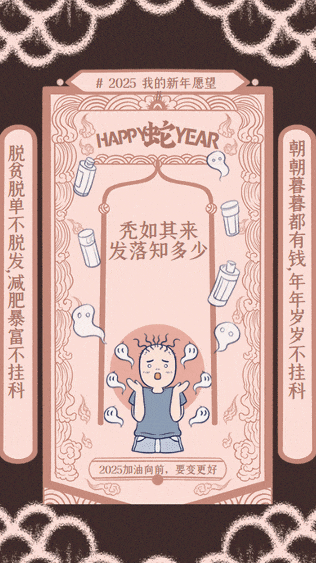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