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乐平市个体户注销一般多少费用(注销个体户要多少钱)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注销个体工商户一般收费多少进行解释,注销个体工商户一般收费多少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本文目录一览:
乐平市国家税务局机构设置
乐平市国家税务局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正科级单位,内部结构复杂,包含11个内设机构、1个事业单位、1个直属机构和3个派出机构。办公室作为内设机构,负责机关文秘、会务、档案、督办、综治、信访、保密、税收科研、税收宣传、政务公开、办公用品管理及网站运行和维护等事务。
乐平市国家税务局成立于1994年,为正科级机构,现拥有121名在职职工,其中91人为党员,98人具备本科文凭,23人拥有大专学历,3人在读研究生。单位内部设有11个职能部门,另设有信息中心事业单位以及稽查局直属单位。
党组书记、局长胡清华主持全局全面工作。胡清华,男,1961年6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198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2月参加工作,江西余干县人。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蒋金火协助局长分管人事、收入核算股、涌山分局工作。
一)景德镇市国家税务局景德镇市国家税务局为正处级全职能局,主要承担税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领导和管理所辖区域的税收征收管理,组织税收收入,以及干部任免、队伍建设和纪检监察等职责。根据上述职责,根据工作职责,市局相应设置11个内设机构、3个直属机构、3个事业单位。
在组织架构上,市局下设了多个重要的行政和事业单位,包括稽查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直属税务分局,以及票证中心、机关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等,为高效运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关于乐平市个体户注销一般多少费用(注销个体户要多少钱)和注销个体工商户一般收费多少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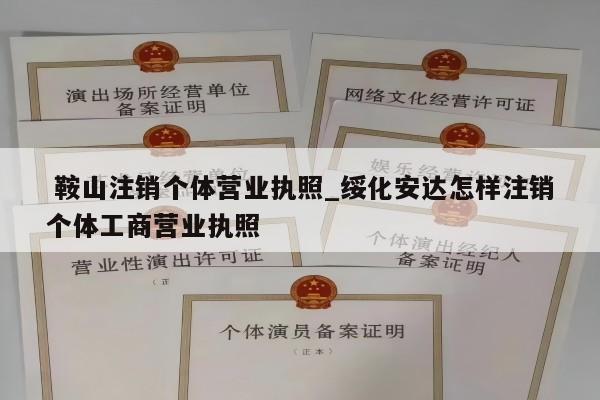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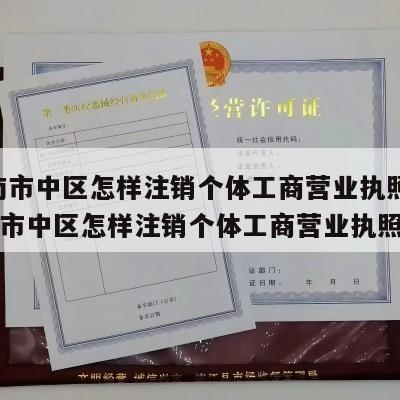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