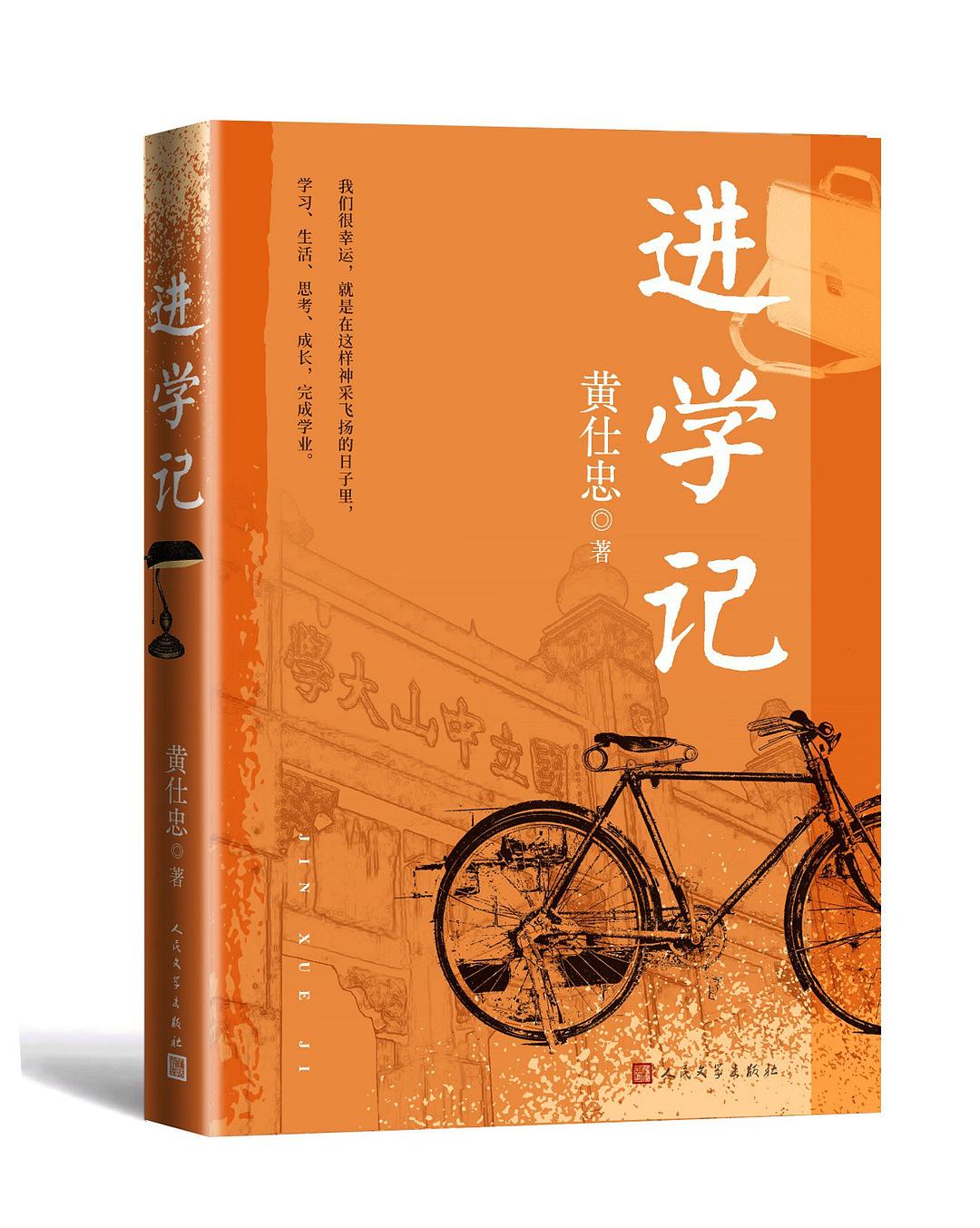
《进学记》,黄仕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进学”二字,无疑会让人想到韩愈的《进学解》。韩昌黎设问解嘲以抒发仕途沉浮的不平之气,固然令人印象深刻,却也客观呈现了个人进学的轨迹,足以激励国子监诸生。就此而言,黄仕忠先生最新出版的散文集《进学记》亦堪称一部“进学解”,它展现了一个学者的“进学”历程,是一个学人对自己学术之路的忠实记录。本书一些文章已收入四年前出版的《书的诱惑》,此次则围绕“进学”重新结集篇目,并新撰写一系列文章,记录“从读书求学、访书问学到指导学生的一些人和事”(陈定方《进学记·序》),主题也更为集中。读者在阅读时,俨然能看到一个学者如何接续前贤的学术滋养,进而浇灌给后进学者,也即一个学者在获得学术的进学经验之后,如何将其介绍给后学。
黄仕忠先生在《进学记》的“问学之路”“从师岁月”“师友往事”三辑,特别是追忆王季思、徐朔方、波多野太郎、曾永义等先生的文章中,详细记叙了从师辈那里获得的进学经验,展现了师辈学人身上的治学三重境界。
其一是学人个体在学术领域能有何为。作者笔下的学者或推动了学科的建设,或开拓了研究的领域,所取得的个体成就有目共睹,因此作者的记叙重点并不在于复述这些成就,而着意于探求他们取得如此大成就的治学经验。这在追忆徐朔方先生的《徐门问学记》《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以及多次提到他的《长留双眼看春星》这三篇文章中,展现得尤其充分。
作者认为徐先生是“自己悟通学术之路”(《长留双眼看春星》)的典范,是学者凭靠个人才智可以取得何等成就的典型,因此对其“自学成才”的经验记载尤详。在《徐门问学记》一文中,作者称徐先生对于学问之道,往往是“在说到某一具体问题、具体观点,顺带说到致误的原因时,才予以指出”。例如徐先生围绕己作《汤显祖与晚明文艺思潮》的讲解,提出了对于使用材料富有启发性的经验,或称“必须注意到将材料本身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从作家们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或称“考证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却不可以不加择别地予以相信”,或称“写论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论文所表现的,应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则在水面以下”,等等。徐先生本人非常重视材料,其厚厚三大本《晚明曲家年谱》的完成正得益于许多新材料的发现,然而他却认为材料对于学术成就的高低并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的资料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资料太缺乏的地方,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过来说,许多学者处于资料条件很好的地方,并没有做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绩,也说明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相较于材料,徐先生特别强调“人”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无异于清醒剂、当头棒。与此相关的是徐先生对于个体悟性的看重,“主张不作干预,让研究生自己领悟;只有能领悟者,才有资格成为合格学者,否则便不当入此门”(《长留双眼看春星》)。其本人从外国文学转向中国文学,从创作转向研究,在古代小说戏曲领域践行“双轨并行”,引领学术思潮(《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恰是“悟通学术之路”最好的写照。这与他主张“学术是个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一脉相承。
其二是融入团队的学人在学术领域能有何为。作者记叙自己从江南负笈岭南求学、追随王季思先生进学之后,注意到王先生“因年逾八旬,特别重视学问的薪火相传”,要以“群体的学问”来弥补个人之不足,遂意识到学术团队的重要性(《徐门问学记》)。在为《玉轮轩曲论》所写编校后记《东廊又见月轮出》一文中,更不无自豪地提到上世纪末古代文学领域两个令人羡慕的学术团队,其中之一就是王先生所带领的。作者记叙了追随王先生进学期间时时能体察到的王先生对学术团队的用心良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定期举行的集体研讨课,中年一代、年轻教师、博士生、硕士生齐聚一堂,就像一次次内部学术交流,成为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延续至今的传统(《我心飞扬》)。作者还记叙了1986年随王先生赴山西临汾参加戏曲研讨会时王先生的叮嘱:“你们年轻人,要与年轻人交朋友,那是一生的朋友。”这种鼓励年轻人彼此交流,俨然是对一种新的学术团队形式——“共同体”的召唤。
其三是个体依靠学术在时代中能有何为。学术何为?每个从事学术的人都要回应这个问题。或为稻粱谋,或向世人证明自己,或寻求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或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等,这些是绝大多数学人的学术状态。其间亦有深具雄大力量者更进一步,将学术与时代相牵连,以学术推动时代的前进。作者笔下的波多野太郎、曾永义先生无疑属于这一群体。从波多野太郎先生身上,我们既看到一个学者因与中国的交游而改变了学术的志向,也看到一个学者在特殊年代以学术为纽带致力于推动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泽被至今(《江南词客潇洒》)。从曾永义先生身上,我们更看到一个学者为打破因历史之故造成的两岸交流阻碍,所做出的“另类”努力。与对徐朔方、王季思两位先生的追忆不同,作者略谈曾先生个人的学术成就,而关注其对学界的贡献;又略一提到曾先生的戏曲研究学科建设、学术组织、后学培养等工作,而聚焦于“酒”事(特别是倡导建立“酒党”一事)。这固然可见传统文人与酒之间难舍难分的情缘,而更重要的是:“那时两岸学者之间有许多话题比较敏感,所以大家努力建立一种亲切的关系,避免不适当言语影响双方的情感。所以在会上谈学问,在会下讲交情,通过酒党与酒文化,很快就拉近了关系,这其实是‘党魁’智慧的一种表现。”(《且饮美酒登高楼》)这番文字准确把握住了曾先生为沟通两岸学术、民间交流所做努力的时代贡献,是以学术推动时代前进之一例。
黄仕忠先生真实地记录了前辈学人身上的治学境界,而随着其进学中身份的转变,“也自然而然地从个体的学术研究,融入一个团队、一个共同体,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这个学术团队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的学术经历》)。这也是作者经历治学三重境界的过程。
《我的学术经历》一文详细记叙黄先生从研究生课程论文开始,到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几乎每一个重要成果的选题、思考、写作全过程,将从徐朔方先生那里感受到“一切以学术为本位”坚守践行,读来令人深受启发。文中也写到自己学术的停顿与徘徊,以及经过十年蛰伏与努力之后的硕果,“完成了自我的学术转型,得以在更宽广的视野下来规划学术,用较长的时段来耐心展开,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学术之路”。伴随着这次转型,黄先生更加意识到学术团队的重要性,并将个体的学术经验推广到团队当中。黄先生的学术团队是从与学生合作开始的,他特别强调自己的学生“在未来也是合作的伙伴”(《此中有真意》),既接续了中山大学的学术传统,也显现出比团结同事更紧密的学术团队构想。黄先生与弟子一道做了许多前人未能做到之事,特别是在俗文学领域,共同完成《子弟书全集》《新编子弟书总目》的出版,一起调查汇集广州府属木鱼书、龙舟歌、南音、粤剧及潮州歌册、闽台歌仔册等,都已取得了硕果。
这次转型也使黄先生意识到治学不仅仅是个人学术的精进,更是鼓励团队中每个个体的进学之路。这种学术团队责任感体现在为后学所作书序中,《进学记》专门收录“学人书序”一辑,其中有4篇是为学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撰序。此举虽是仿效曾永义先生“对年轻学者的呵护与勉励之意”,却也有自己的思考,“着重在著作背后的故事,借此记录他们的问学经历,记录我们合作展开学术探索的过程”(《进学记·后记》)。这在为学生李芳所作序《此中有真意》一文中,有着更加丰富的阐述:
我希望我的博士生,选一个合适的对象,圈出一块领域,构建自己的“根据地”,通过三五年的开垦,完成基础文献的寻访,然后写成博士论文;再用三五年时间继续深入,在全面阅读所获文献的基础上,识其全貌,然后编制完成总目或叙录;再以三五年时间深入到文本内部有关问题,同时结合整个学术领域,打通其他体裁,那么,用十到十五年时间,就可以让一个领域从基础文献整理到专题内容研究都得到全面推进,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专门家”。
如此细心而方向性明确的指导,真可谓“授之以渔”“金针度人”。这一规划既来自个人的学术转型,也得益于王季思先生的教诲:“一个人,一生中若能有三十年用于学术,每三五年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如此持之以恒,待到耄耋之年,便自然是博学之士了。”(《我心飞扬·附:学者之域》)不过黄先生所提供的从学、治学、进学的经验,相对更加具体而微,堪称“一套自己的工作程序”:首先是全世界范围内对文献作全面系统的调查、编纂目录,其次是力求对其中珍稀文献复制或出版,最后是完成一部研究著作,尤其是要有以十到十五年为周期展开专题领域研究的毅力(《此中有真意》)。黄先生所给出的路径,像是最笨拙的,却又是最便捷的。
更进一步,黄先生也从不认为学术仅仅是个人或师门之事,这既是受到前辈学人学行的熏陶,又因为其“个人的‘进学’,始终与家国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行进的步伐,永远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后记》)。因此,黄先生在《进学记》中收录的文章又往往有着弦外之音,如为学生作序是“着意写成不同领域的学术史记录”(陈定方《序》),如对徐朔方先生的追忆是“借此回顾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思想学术变迁史”(《后记》),均为观察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绝好样本。基于这样的思考与时代责任,黄仕忠先生与学术团队在2016年创办了《戏曲与俗文学研究》刊物,又于次年筹办了“戏曲与俗文学研讨会”,建立起一个超越同代友人、师门师承关系,能够沟通前辈与后学、跨越地域、大陆与境外的“学术共同体”。这又无疑是在学术领域为时代做出贡献。
倘若说个体的学术精进、追求与成就是一种“自度”的话,那么培育弟子、作育英才就是“他度”,而创办学术刊物、搭建学术平台更像是一种“普度”了。不仅如此,黄先生又将自己的进学经验形诸笔端,化身百千,超出师门限制,向广大年轻学者传授“学林秘籍”,则又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布施”了。
这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无疑有着压舱石、镇静剂之功效。一方面博士生越来越多,经典选题越来越少,如何才能在同类、同样题目中有新见?黄先生在《此中有真意》一文中,针对首位博士生李芳面临的“崩溃”心理——已经寻访了大量材料,却发现已有一篇完成的同题博士论文,内容又是自己所设想的——给出了振奋人心的劝慰:“在你还没有对这个专题展开真正的调查与研究之前,单凭印象中的研究范式,所设计出来的章节、内容,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的观点、想法是要通过文献研读之后才确立起来的,所以要有信心,只要继续按计划实施,最后要担心的不是没内容可写,而是内容太多,写不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虽是针对个案而言,又何尝不能破除其他方向研究的“困境”。
另一方面论文考核越来越重要,如何才能兼顾考核压力与学术要求?黄先生也曾因文章“写得太多,太快了”而受到导师的批评,意识到“太多,则意味读得太少;太快,则仍未去其浮躁”。这番自我反思在今天是否“正确而过时”了呢?黄先生基于自己的经历,发现“某些学术问题数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无人来‘抢’;或则既为独特思考结果,必与人不相重复,也无可与争”(《徐门问学记》),可谓肺腑良言。对于古典文学文献学研究而言,这一点又在对新材料的态度上有充分的体现。为了着其先鞭,占有新材料发现者的荣誉,且能得到一篇论文,甚至一种材料的发现有可能更新对学术史某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为学人所看重,所以许多学者不得不在发现新材料之后快速落笔,而缺乏深刻的考索。在黄先生看来材料无疑是重要的,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的完成得美国图书馆所藏材料助益颇多,其本人与日藏中国戏曲小说文献有关工作的完成也无不与材料的丰富有关,而其指导学生更是提倡“竭泽而渔”式的“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面系统的文献调查”。但相较于占有材料,黄先生与徐朔方先生一样更重视材料的使用:徐先生认为“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黄先生也认为“在今天,许多原本珍贵无比的材料,渐次影印出版,却并未见到学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徐门问学记》)等,都是针对个体治学的不可多得的经验。真正的研究,就要深入地搜集、阅读文献,从具体材料出发,而非先有范式框架,再将材料进行填充。
今天的学者还面临学术在为己与利他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元好问曾有诗云,“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当学术被简化成一篇又一篇论文、一个又一个项目,甚且与个人职称高低、生活质量好坏直接挂钩的机制时,一个学者就不得不将学术逐渐窄化为为己的,不仅材料密不示人,就连治学方法亦不肯外传。这恰是《进学记》这本“进学”随笔集问世的价值所在。黄先生像他的师辈一样,“要把金针度与人”,将自己获得的学术作为天下公器之“道”分享出来。
更进一步,黄仕忠先生《进学记》中完整呈现的从“自度”到“他度”,再到“普度”的学术金针,在其同时代学者身上具有一种共性。他们这一代学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代真正跨越时空限制而能阔步走向校外、省外乃至境外,进行频繁且深度交流的学者,尽管也曾有过如韩文公那样的“迷茫”,却也像韩文公那样在个体取得学术成就之后,热情致力于作育人才、奖掖后进、传承学术,或坚守讲台,或公开讲学,或举办论坛,或搭建平台,或像黄先生一样将金针化身百千,无不是“要把金针度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学记》无疑是这一代学人“进学金针”的写照。
——————————
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赏》2025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