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37 年,大宋景祐四年,大辽重熙六年。
这一年,是宋仁宗亲政的第四年了,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大事,但是你细品,这一年其实有很强的辞旧迎新的意味啊。
说到“辞旧”,今年,我们要告别一位老朋友,丁谓。“丁谓”这个名字,你要是觉得还不太耳熟,可以出门左转,去看《文明之旅》1021年的那期节目,专门讲他的。在宋真宗那一朝,他虽然名声不是很好,但是能量极大,谁也不敢小瞧。就说今年6月份他去世,宰相王曾听说之后,松了一口气说,“丁谓这个人啊,太聪明了。他要是不死,没准皇上还得用他。到那个时候,他可就是个祸害喽。”王曾还特别声明,“我这可不是幸灾乐祸啊。”你看看,丁谓被贬出朝廷已经十几年了,正式退休也已经四年了,所谓“猛虎虽老,余威犹在”,说的就是他这种情况。
丁谓这一死,宋真宗一朝的那些名臣,什么王旦、寇准、曹利用、丁谓、王钦若,就算是凋谢殆尽了,一个时代彻底落幕。
不是说“辞旧迎新”吗?那这一年我们迎来的新人是谁呢?苏东坡啊。你现在到网上搜1037这一年,大概率搜到的都是苏东坡。可以说,这一年就是因为他而被载入历史的。今年1月8日凌晨,大概五六点的时候,他降生在四川眉州,从此大闹人间64年。未来64年,他留在世间的那些长吟短叹、欢声笑语,直到今天还听得见。
我说这一年有强烈的辞旧迎新的意味,还不止于此。这两年,大宋朝堂上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定睛一看,论战的背后,其实还有两个人群之间的隐隐然的对立,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叫“党争”,两伙朋党之间的争斗。这不是“景祐”年间吗?所以,这次党争史称“景祐党争”。
再定睛一看,党争的背后,其实是新老两代人之间的摩擦。老人没有丁谓这么老,新人也没苏东坡这么新,而是介于这两代人之间。所谓老人,就是这几期节目里我们偶尔都会提到的吕夷简,而新人的领袖,则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
好,1037这一年,我们就来看看这新老两代人争的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一定要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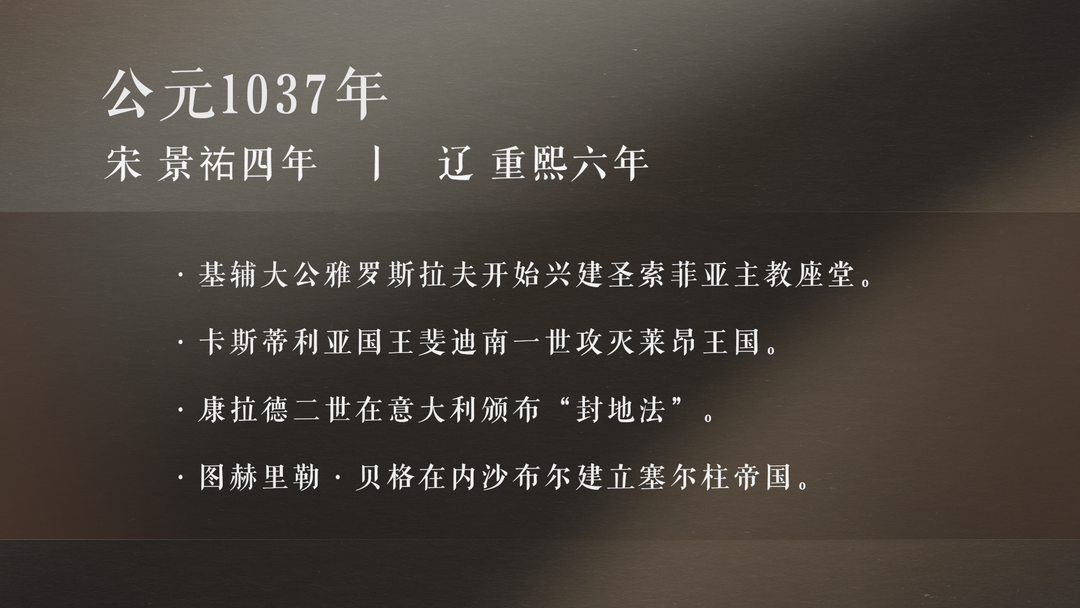
新老两代人
刚才我们说到景祐党争。你一听就会想,他们到底争个啥,对吧?
我可以提前剧透一下,其实啥也没争。就是我说你道德不行,他说我道德不行,争来争去是一场口水战。我们一会儿再讲。所以你就知道,这场党争,本质上是新老两代人之间,互相看不惯的那种摩擦。我们就得花点时间捋捋这大宋朝的士大夫这一代和另外一代之间的代际关系。
一代新人换旧人,不只是岁数大小的问题,一代和一代之间,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
大宋朝第一代士大夫,最典型的是宰相赵普,就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位。这一代人大多数生于10世纪的前30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10后和20后。你想,大宋建立是960年,他们正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正是年富力强好干活的时候。
严格地说,这一代人都不算是宋朝人,他们生在五代、长在五代,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也形成于五代。其中有的人,比如赵普,很走运,一开始就跟对了人,跟着赵匡胤成了开国元勋。还有的人,在五代时候就是职业官僚,被大宋朝继承下来了。比如,宰相范质,就是后唐的进士,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官儿他都当过。大宋来了?好,我是小车不倒尽管推啊,接着当官。这一代人在宋真宗即位之前,差不多就都去世了。这是大宋士大夫 1.0 。

第二代士大夫我们就很熟悉了,都是咱们《文明之旅》前面讲过的老朋友,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旦、丁谓、王钦若,这一代人大多是10世纪的 40、50和 60 后。
他们的履历就比较相似了,是宋朝初年扩大科举的受益者,大多是太宗朝的进士。吕蒙正是太平兴国二年的状元,李沆、寇准和王旦都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丁谓和王钦若都是淳化三年的进士。这都是宋太宗的年号。可以说,他们是大宋朝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士大夫。这一代人到了今年,基本上七八十岁了,差不多都去世了,丁谓算是其中最后一个凋谢的名人。这是大宋士大夫2.0。

这一代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家世普遍都不错。对啊,他们自己是大宋朝的人,但他父亲可都是五代的人啊。在那个乱世,还有能力培养孩子读书的,家里一般都是有根基的。这还不只是说家里有钱,而是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上层社会的关系网里面的。我们以前就讲过这个话题:在科举成熟之前,一个家族要想延续自己,怎么办?除了给子女更多的教育资源之外,就是要跟其他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啊。所以,这一代士大夫,互相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那再接下来的3.0版的士大夫什么样呢?就是现在1037年这个时候当政的这批人,吕夷简、王曾、李迪、韩亿这些人。他们主要是10世纪的70后,大多是真宗朝,也就是11世纪初考中的进士。

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三个字,“好孩子”,被老一辈看中之后,一步步刻意培养起来的好孩子。
比如韩亿,刚中了进士,就被宰相王旦相中,把女儿嫁给了他。王旦家里人刚开始还反对,因为韩亿结过婚,还有个儿子,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拖油瓶的鳏夫。王旦说自己家里人:你们懂什么?然后强行就做了主,认韩亿做了女婿。事实证明,王旦眼光不错,韩亿后来果然当到了参知政事副宰相。而且韩亿的后人,成为北宋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再比如王曾,那是连中三元的状元,在中国的千年科举史上,也是响当当的传奇人物。是不是邻居家的好孩子?王曾是同时被李沆和吕蒙正两家同时相中,后来成了宰相李沆的女婿。你看,也因为是好孩子,成了被宰相刻意栽培的人物。
还有现在那个宰相吕夷简,那就更典型了。他干脆就是前朝宰相吕蒙正的侄子。话说吕蒙正退休得比较早,景德年间,就是本世纪初年就退休,住到洛阳去了。后来宋真宗到处跑着搞祭祀,正好路过洛阳,就去看望老臣吕蒙正。真宗就问吕蒙正,你几个儿子里面,有可用的人才吗?很明显,这是皇帝想给老臣一些好处,帮他关照一下儿子。吕蒙正的回答很出人意料,他说,我几个儿子都不行。但是我有个侄儿,叫吕夷简,这是个当宰相的材料。你可以试试用起来。虽然是叔侄关系,但是你从这个故事里也看得出来,吕蒙正是真的喜欢“好孩子”吕夷简。
讲完这几个故事,你脑子里应该勾画得出来这一代3.0士大夫的形象了:从小学习好,尊敬长辈,少年老成,有宰辅气象。看一眼就知道前途远大,年轻的时候就被长辈看中,然后一路栽培成长起来的。那这种人成了朝廷骨干之后,执政的风格也一定是偏向沉稳持重这一路的。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就说,你看,从真宗到仁宗初年,这一批的士大夫,都是厚重之人啊,多亏了李沆那一代的提拔啊。这是第三代。
好,那再接下来的第四代士大夫,也就是今年这一期提到的政坛新人,情况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一代人,一般都是出生在11世纪了,是00后。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年是1037年嘛,你看,后来的大文豪欧阳修今年31岁,后来的名相韩琦30岁,名相富弼33岁,还有跟宋代诗歌的开山祖师梅尧臣齐名的苏舜钦,这个时候还不到30岁。这拨人当中,只有范仲淹岁数比较大,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尾出生的人,比欧阳修这拨人大上个十几二十岁,所以,范仲淹也是这批人中的大哥大。
那除了年轻,他们和吕夷简那代人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有啊。如果说吕夷简他们是“好孩子一代”,范仲淹他们可就是“苦孩子一代”了。为啥?因为科举。你想,科举到了真宗朝的时候,可是越来越公平公正了。只要自己有本事,寒门也能出贵子。
就拿范仲淹和欧阳修这二位来说,那真的是贫苦出身。范仲淹两岁丧父,跟着母亲改嫁到别人家,成年后才知道自己应该姓范,就自己一个人跑到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苦读。范仲淹不是还留下了一个著名的传说吗?说早上煮一锅粥,冻成固体,然后分成四块,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随便撒点蔬菜和盐,就这么吃了三年。这还是个成语,叫“断齑画粥”。欧阳修也没好到哪去,四岁丧父,母亲带他投奔亲戚,问题是亲戚家也不富裕,所以从小就过得很拮据。在穷这个方面,欧阳修也留下了一个成语典故,叫“画荻教子”,说他的妈妈亲自教他文化,但是没有钱买纸笔,就掰根草棍子在地上教他写字。宋代士大夫是到了这一代人,才开始出现这类从小很穷的故事的。
请注意,苦孩子可不止是“穷”,我们一层层地来看,这帮新崛起的苦孩子出身的士大夫,他们身上还有什么特点?
首先一条,他们没有原生的上层社会关系网。对啊,穷家小户出身,即使当官之后,遇见一个年纪大的官员,也攀不上什么“世伯”、“世叔”、“家父命我向您问好”之类的交情。所以,原来朝廷中的那些盘根错节,互相之间的人情往还,他们不知道、不关心、不忌讳。
好,不忌讳人情,对于身在关系网中的人来说,这就是楞,就是冲动,就是幼稚。这就带来了这批苦孩子士大夫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很难和老一辈的人形成那种师徒父子的感情和传帮带的关系。你不听话嘛。
我举个例子。话说当年刘太后还在,宋仁宗还没有亲政的时候,有一年冬至,仁宗率百官朝贺刘太后。范仲淹看不惯,一封奏折就上去了。说,“咱们这位天子,在后宫给太后磕个头什么的,都行,那是你们家人之间的礼数。但这可是朝堂啊,天子至高无上,哪还能给人行礼呢?这么干,损害了皇帝的权威,不行的啊。”
这话说得很有勇气,但是在有的人看来,这话说得就太楞了。其中有一个人就被吓坏了。谁啊?大词人晏殊。晏殊本来比范仲淹还小两岁,但是因为晏殊是神童啊,中科举比范仲淹要早10年,所以也算是范仲淹的前辈。晏殊本来对范仲淹很好,一路关照、提拔、推荐,但是他可能也没想到范仲淹这么楞,居然直接冲撞刘太后,就跑去质问他,说你自己作死我管不着,但是你这会拖累推荐你的人的,你要害死我了。
范仲淹脖子一梗,那话说的,“您抬举我,我一直担心自己配不上您的抬举。但是没想到,我是因为自己道德高尚,又忠诚又耿直,才配不上您的。”把晏殊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对啊,我跟你谈交情,你跟我谈道德,这个天儿还怎么聊?范仲淹还不解恨,回头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信,又把这个道理说了一遍,一点面子也不给晏殊。晏殊最后只好说,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咂摸一下这个故事。这里面当然有性格冲突,但更本质的原因是,范仲淹不觉得自己是在你们那些朝廷大佬编织的关系网里,你们在意的那些交情,那些羁绊,跟我说不着。我就根据自己内心的朴素的道德直觉来做事。你说,遇到这样的后生,前辈们怎么栽培提携?惹不起嘛。这是这一代士大夫的第二个特征:不听话、不就范。
其实,他们还有第三个特征。你想,虽然是苦孩子,没有天然的上层关系网,但是人的天性就是要结群、要抱团的。他们从小镇做题家突然变成了官僚集团的一员,他们能和谁抱团?当然就是和自己出身类似的年轻官员抱团啊。
我自己有一个观察。有的机关单位,或者是公司里,有些资深员工,甚至已经做到了中层,互相关系特别好,一追溯,很多都是当年一起进单位进公司,一起住过单身宿舍的一帮人。今天的关系,是从当年一起吃食堂,一起加班,一起聊天的交情发展来的。还有那么个词,叫“职场发小”。说到底,是因为命运相同,经历相同,甚至价值观也相通。
这批宋代年轻士大夫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都在开封举目无亲,那还不抱团?抱团的时候,你想都想得到,经常聊天的话题,一定是觉得自己道德高尚,而那帮在位的年长官僚,要么是老朽无能,要么是品行卑劣。而反过来,那些年长的在位官僚,又会怎么看这帮年轻的士大夫?一定会觉得他们是一帮不识大体、不讲规矩、只有一腔血气之勇的闯祸小孩儿嘛。
说到这儿,你明白了吧?公元1037年,大宋景祐四年发生的新老两代士大夫的摩擦,简直就是必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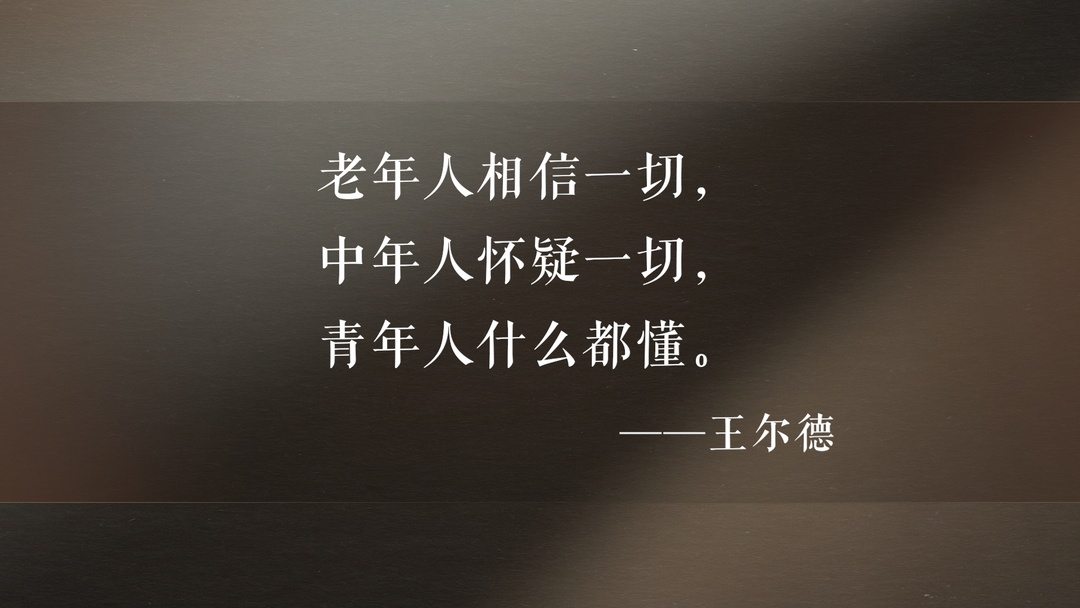
对错两本账
刚才我们分析的,是两代士大夫之间的代际冲突。其实,还有更复杂的大背景。我这里只说两条。
第一条是,大宋朝到了这个时候,阶层上升的机会变得相对集中了。
你想,宋朝建国这70多年,可是一直在坚定地推进一件事:把地方上的权力一点点地收到中央来。这本身无可厚非,吸取五代的教训嘛。强干弱枝,那是国策。但这也带来了一项后果,那就是读书人的出路变窄了。原来,一个读书人,即使考不取科举,也可以到一个地方官的幕府里讨口饭吃。比如唐代的李白、杜甫,一辈子基本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朝廷中央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上升机会。一个大宋朝的年轻读书人,只有到开封,才能找到出路。
那中央的机会多吗?朝廷已经很努力了。比如三年前,宋仁宗直接把科举进士的录取比例,从百分之六七,拉到百分之二十,而且这个数字不是临时的,是他在位期间的标准录取率,比如,1034年,就冒出 783 个新科进士。按说这是为读书人拓宽了出路。但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考取了进士,你得让我当官啊。这官职数量又不够,所以又有大量的新科进士在开封城等着分配工作。这个僧多粥少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啊。

那你想,底层的年轻士大夫们什么感受?当然是觉得上升之路越来越难。他们一腔愤怒能泼向何处?其中之一,当然就是当权的老一代啊。就因为你们挡路,才让我们晋身无门啊。这是新老两代摩擦的又一个大背景。
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从宋真宗开始推行的“台谏合一”。
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就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功能越来越一致。本来,御史台是负责监督官员的机构,是从上往下挑毛病的;谏院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是从下往上挑毛病的。工作对象本来不同,但既然你们都是负责提意见的,那就干脆都能提吧,职务的边界就没有那么清楚了。表面上这就是一个机构改革的事,但其实它的后果很深远。
台谏合一了,这可是专门负责提意见的部门啊,那你说,这个部门的官员谁来任命呢?宰相吗?不合适吧?宋仁宗就说过嘛,如果台谏官员也是你们宰相挑选的,那宰相的过失,谁还敢说话呢?所以,台谏官员的任命权到了皇帝手里。
好,那下一个问题,皇帝任命的台谏官,你说是挑皇帝的毛病多呢?还是宰相的毛病多呢?不言而喻嘛,当然是宰相。而且,就算挑皇帝的毛病多,那又怎么样?皇帝又不能换。顶多点点头,说你说得好,我下次注意。但是台谏官的锋芒如果指向宰相,宰相就得主动回家待罪,或者辩解,或者至少得申请辞职。
你看,这台谏官是皇权制约相权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政治工具。就算皇帝不搞什么小动作,有这么一个天天准备挑朝政毛病的机构在,你想,宰相会不会如芒刺在背?
好,再下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被任命为台谏官?当然是年轻的、地位比较低的官员。年轻,所以有闯劲儿,地位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多顾忌。哎?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出生穷苦,现在又上升无门的年轻官员吗?
好,明白了这个背景,你就知道在1037年,以范仲淹为首的这批年轻台谏官和以吕夷简为首的这批老宰相之间,为什么一定会发生摩擦了。
不过,在这里我要强调:刚才说的那些都只是时代背景和外在条件。并不是说,因为穷,因为没有关系网,因为缺乏上进之路,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就和老一辈闹。没有这个意思。接下来你会看到,范仲淹、欧阳修这批人之所以会在中华文明史上成为如此光彩夺目的存在,究其根本,仍然是他们的圣贤人格和内心的道德勇气。
好,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今天的主题了,“景祐党争”是像唐代的“牛李党争”一样,持续时间长,斗争惨烈的朋党争斗吗?其实没有。就是电光火石地那么几个回合。我们简单地捋捋事情的经过。
第一个回合,是范仲淹主动出手。
他上一年,1036年才被调回开封任职,代理开封知府。他画了一张图,叫“百官图”,送了上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朝廷里的各种人的关系,或者说是他以为的关系都列在上面,你看看,“给这个人升官,就按规矩来,给那个人升官,就是不讲规矩,对待这个人,就是有公心,对待那个人,就是有私心。”这是要干嘛?就是冲宰相吕夷简去的。说吕夷简用人有私心。不过这个出招的方法,也是匪夷所思,你告吕夷简的状就说吕夷简的事儿呗,你画个“百官图”,这不是要把朝廷里所有的官儿都得罪了吗?
你看,这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对范仲淹来说,无所谓,我不是你们那个牵牵绊绊的关系网络里的人,我是一代新人,我内心里有一腔道德勇气,我怕啥。
站在吕夷简的角度看,这种攻击肯定也没啥道理。我是宰相,而且是从刘太后当朝的时候,我就是宰相,到现在已经9年了,我用人,当然有我的道理。我看中的人,升迁快了一点,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至于你指责我,是出自公心,还是私心,这有啥客观标准可言?你范仲淹到皇帝那里告我这种刁状,又没有什么证据,有啥用?所以,吕夷简并没有针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击的动作。史料上记载,他只是不高兴而已。
第二个回合,是吕夷简出手攻击的范仲淹。
有一次,仁宗皇帝拿范仲淹的一个政策建议问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没正面回答,只说范仲淹这人说话不切实际,而且贪慕虚名。按照当时的那个格局,其实我挺理解吕夷简为啥这么说,掌权的老宰相遇到范仲淹这样的耿直青年,有这样的评价是很正常的事。但是,请注意,吕夷简这个时候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开始搞起了人身攻击。
范仲淹一听,也急了,连续上了四道奏折,那你想,里头能有什么好听的话?每篇都话里话外点了吕夷简。吕夷简就真急眼了,掰着手指头,在宋仁宗面前说了范仲淹三个问题:第一,你越职言事。你范仲淹是开封知府,你现在说的这些事,是你该操的心吗?这是程序问题。第二,你搞朋党。你们这帮年轻人,一伙一伙的,想要干什么?这是品德问题。第三,你离间我们君臣关系。这是个动机问题。
范仲淹马上反唇相讥,连续上书,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事情闹到这个局面,反正就是逼当家的宋仁宗要做一个决断了。这两个人,要么选择一个留下,要么两个都不要了。最后,宋仁宗决定,牺牲范仲淹,把他贬出开封城。这是上一年发生的事。
那你说这就完了吗?并没有。到现在为止,好像是吕夷简全胜,范仲淹落败。但是到了今年,吕夷简也被罢相。而被贬出开封的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也发生了一点变动。什么啊?就是他们当官的地方,离开封近了一点。范仲淹原来是被贬到饶州当知州,在今天的江西。那今年呢,朝廷让他去润州当知州,就是今天江苏的镇江。你看,离开封近了不少。还有,欧阳修,上一年是被贬为夷陵县令,在今天的湖北宜昌;今年也挪动了,到光化县当县令,在今天的襄樊。你看,也是离开封近了。在当时,这是朝廷释放的一个明显的信号,让天下人都知道,去年被贬出去的这批人的政治处境正在好转。

你看,到今年为止,这新老两代士大夫的一番口水大战,先是打了个两败俱伤,最后一看,其实是打了个势均力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预告:过几年,因为西夏的军事压力,朝廷又到了用人之际,这两批人又被召回启用,而且还言归于好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你听听这个过程,双方基本上都是隔空过招,在皇帝面前互相告状,连当面翻脸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次冲突的烈度并不高。那为什么在历史上还是留下了“景祐党争”这个名字呢?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党争”可不是什么好词,它的潜台词是:这就是两伙人乱斗,而且没有什么是非可言。
那这次是不是党争呢?这就需要再进一步去深入细节去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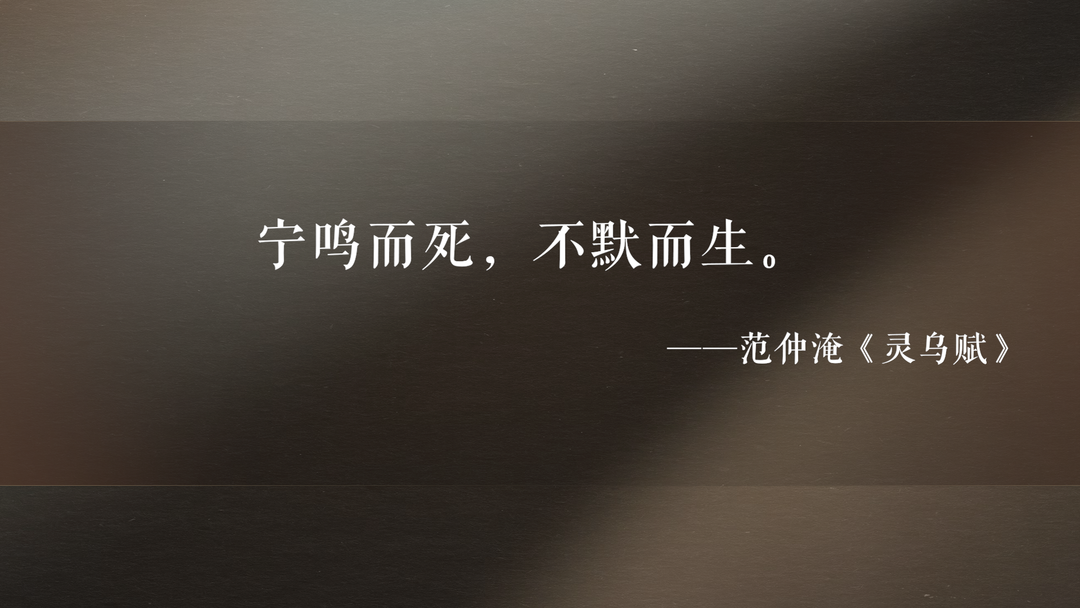
理想两条路
好,我们回到那个问题:景祐年间发生的这新老两代士大夫的摩擦,到底算不算党争?
至少有两点很像党争。
第一点,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策分歧。反正从现存的史料里面看不出什么分歧。大家指责的都是对方的人品。
第二点,就是确实是有团伙。
老一代人参战的,似乎只有吕夷简一个人。但是你想,到这一年为止,吕夷简已经当了9年的宰相。只有他参战,是因为他的目标最大,但他的身后肯定是有明里暗里的大量支持者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的。更进一步地说,在位的宰相,即使自己不结党,也自然会有人上来迎合。比如这次,范仲淹刚被贬,有一个官员叫韩渎的就公开说,咱得把范仲淹的朋党名单拉出来公示,以后再想越职言事,就是超出自己本职工作瞎哔哔的,都要以此为戒。宋仁宗还就答应了。史书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下了几个字的断语,说“韩渎希夷简意”,他是在迎合吕夷简。你看,在位的大佬,是从来不会缺这种送上门的便宜同伙的。
那另一边呢?新一代士大夫参战的,表面上是范仲淹,但背后其实是一批政坛年轻人。比如,欧阳修、尹洙、余靖、蔡襄这些人。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句:前面我们说了“台谏合一”的大背景,而这个时候的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并不都是台谏官。但是,他们此前或此后,都有当台谏官的经历。
他们抱团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明知道范仲淹把皇帝和宰相都得罪了,还是纷纷上书,飞蛾投火般地营救,导致这批人也纷纷贬官。请注意,这种营救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行动,是有组织的。
举个例子。欧阳修后来自己说,他就参加过一次对范仲淹的营救策划会。参加这次聚会的,一共有四个人,除了欧阳修年龄较小,是天圣八年进士,其他三个,都是天圣二年进士。你看,这是科举同年的关系,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容易抱团的一帮年轻人。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同年里面,有一个当场跟他们吵翻了。这个人高若讷,他说,我就看不惯范仲淹,他这个人性格太急躁,说话太狂,有这个结果是自取其辱。结果呢?营救策划会演化成了内部人声讨叛徒。
欧阳修后来写了一封很有名的文章,《与高司谏书》,就是痛骂高若讷的。其中那话说的,“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还有,蔡襄,就是书法史上的宋代四大家“苏黄米蔡”之一的那个蔡,蔡襄写了五首诗,叫《四贤一不肖诗》,写给五个人,一人一首。乍一听,这“四贤”里肯定有范仲淹和欧阳修,还有余靖和尹洙,这“一不肖”指谁呢?想来应该是指吕夷简吧?非也,非也,那“一不肖”,就是那个看不惯范仲淹的同年高若讷。你看,这确实是小团伙才有的现象:最恨的不是敌人,而是原以为是自己人的叛徒。
那你说,这是朋党政治吗?这是范仲淹的政敌指责他的词儿,也是当年的皇帝特别在乎的词儿,我们隔了这一千年,完全没有必要去贴这种标签。我们关注的不是这种陈旧的骂名,我们要注意的是新元素:当中华文明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全新的元素,正在加入到政治运作的过程之中。
你想嘛,在一个天下承平、皇权稳固的时候,一帮年轻的、级别不高的官员应该是什么表现?大概率应该是唯唯诺诺的、谄媚钻营的,至少也应该是懂事听话的吧?因为你一辈子的成败利钝,都捏在上司们的手里呢。但是,大宋朝立国70年后,居然出现了这么一帮奇怪的士大夫。他们举起道德的大旗,主动向皇帝、宰相叫板,一个人被惩罚了,剩下的人抱着团地飞蛾投火,我也要求受惩罚。
那他们这是找死吗?有趣的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这帮人不仅没有被迫害、被驱逐出官场,反而最终一个个被重用,甚至是千古流芳。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人: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耀千古;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永世流传;蔡襄,宋四大家之一,中国书法史上永远的大神。这些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芒,到今天还非常闪光。而他们的对立面——吕夷简,今天知道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就算不给他什么恶评,他最多也就算是历史上的一个行政能力还不错的老官僚。仅此而已。
你看,这是一条全新的路,居然也能走通?这让那些在官场上只敢循规蹈矩、等待提拔的人情何以堪啊?
对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新东西,就在宋朝的这个阶段,一条崭新的人生发展道路,突然就走通了,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治逻辑。
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能走通了?这种人就能诞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因为他们是成熟科举制下的新一代,他们是没有受老关系网羁绊的新一代,是少年穷困、长而有志的新一代,但是更重要的,他们是把儒家政治理想带进政治实践的新一代。
这个转折就大了。原来的官员,出身很可能是儒生,但是儒家道德理想。那是自己内心的事,是你个人修养的事,是脑子里面想的;和外在的政治实践,人的外部行动,这是两回事。直到出现了范仲淹、欧阳修这批人,他们的儒家理想主义变了,他们更在意内心的道德力量能不能付诸实践,如何能由内而外,从言到行,从天道到行动,从儒术到政治,这一脉贯通。
这批人的出现,给此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带来了很多变量,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今天只能简单地说两条。
第一条,把内心道德代入到现实政治之后,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后果,就是是非标准变得模糊了。
原来的官场上,是非标准,要么听权威的,比如听皇帝的;要么听结果的,比如看政绩;要么听公论,看大家怎么说。而在道德政治下,麻烦了,这些外在的标准全部消失,一切是非都只听内心的判断。
比如,你吕夷简不是说我们贪慕虚名吗?我范仲淹就写一篇《近名论》,论证一个人看重声名是很有必要的。
你吕夷简不是说范仲淹逾越职权,越职言事吗?范仲淹的朋友就说,大哥确实是越职言事,但大哥是为了清除奸臣才不得不越职言事啊!至于谁是奸臣,我们内心里觉得是,他就是啊。
你吕夷简,不是说我们搞朋党吗?欧阳修后来就写了篇《朋党论》,说君子之间的朋党,跟小人之间的朋党能一样吗?小人结党,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君子结党,那是因为有共同的道义啊。
要是在过去,一旦拿起像“朋党”这样的武器来攻击人,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否认啊,我不是我不是。现在变了:我承认我们是啊,但是根据我内心的道德标准,我们是好朋党。你看,是非标准就撕裂了。大家要是都这么聊天,很容易把天聊死啊。确实,后来到了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时期,两拨人渐渐地互指:我是君子,你是小人,我是忠臣,你是奸贼,到了那个地步,任何理性的、有效的政治对话,就不再可能了。
但是道德政治也不全是坏事。它还带来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对皇权的制约。
你想,皇帝能够控制大臣,用的是什么工具?就是用权柄来操纵祸福啊。升官、贬官、表扬、批评,乃至在你死后给你一个谥号,让你面对后世是有面子还是丢面子,全看皇帝。所以皇帝对大臣有控制力。
但是面对范仲淹这批士大夫,他们依靠的是内心的道德力量,外在的祸福对他们影响力小了,甚至是反了。举个例子,范仲淹三次被贬,第一次是在 1029 年,因为督促刘太后还政被贬,朋友为他饯行,说他“此行极光”,被贬非常光荣;第二次是在 1034 年,朋友说“此行愈光”,更光荣了;第三次是在 1036 年,又是“此行极光”,最最光荣。“三黜三光”,三次被贬,三次光荣。你看,皇帝越使劲往泥土里踩他,他的地位就越高。
再比如说,范仲淹有一个朋友叫尹洙,他看到范仲淹被贬,就上书说,你们不是给范仲淹安了个罪名叫“朋党”吗?那我跟范仲淹关系最好,我也是朋党,你们应该把我连坐了啊。来来来,你们倒是来贬我啊。
站在皇帝的角度看,这事就麻烦了。我贬斥你们,你们应该恐惧,至少应该是沮丧才对。现在倒好,你们觉得光荣,还前赴后继上赶着来求贬斥。我手里的权柄不能给你带来祸福,从今往后,我还怎么操控臣下呢?
所以你看,把儒家道德理想代入到现实政治实践,也给皇权出了个大难题。
我们隔了这一千年,没有必要对这个变化做简单的判断,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在1037年,随着景祐党争的告一段落,我们只需要知道,道德政治来了。这个新元素的加入,让政治舞台上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至于结果是好还是坏,还是得看具体的人。就拿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范仲淹和吕夷简来说,道德政治让他们对立,但他们还是有能力在日后相逢一笑,冰释前嫌。而再往后,道德政治继续演化,有的时候,是一曲壮歌,有的时候,则只是为我们后人留下一声叹息。
没关系,《文明之旅》节目我们就这么捋着时光的绳索,步步向前,此后所有的悲喜剧,我们都看得到。
我们下一年,公元1038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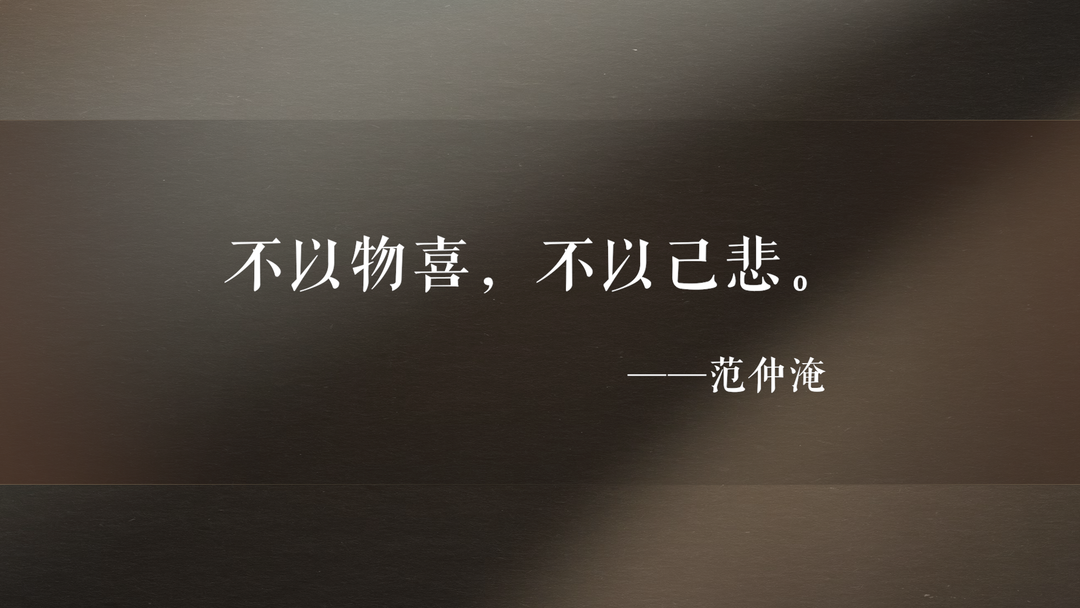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宋)苏辙撰:《龙川别志》,中华书局,1982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宋)司马光撰:《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
(宋)张邦基、范仲撰:《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2002年。
(宋)蔡襄撰:《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宋)欧阳修撰:《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清)王夫之撰:《宋论》,中华书局,2003年。
王启玮:《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
赵冬梅:《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中信出版社,2024年。
[美] 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和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
赵益:《两宋党争:大宋帝国的衰亡》,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英] 崔瑞德:《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 907-12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