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方诚峰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获得学界的好评。十年后,他的新著《君主、道学与宋王朝》面世,自然颇受关注。他的专业是宋史研究,但视野绝不囿于宋史,而有着更宏大的关怀。方诚峰尤以理论思维见长,两书都期望对宋史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提示结构性的把握。怀抱着期待和阅读此书的一点疑问,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采访了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方诚峰先生。

方诚峰
澎湃新闻:2015年您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以下简称“《北宋》”),时隔十年,第二部专著《君主、道学与宋王朝》(以下简称“《宋王朝》”)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在写作《北宋》时,“政治文化”在历史学界如火如荼,可是《宋王朝》并没有继续采用这一概念。这些年您对“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有过怎样的反思?
方诚峰:“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使用得已比较广泛。有时候它被看作一种方法论,如对政治现象、人物的文化解释,或反过来。更多时候政治文化被视为研究对象,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文化现象(在今天被归入文化范畴),如经学、德运、正统、礼仪、祭祀乃至宗教,等等。这两种取向也会交叉。《北宋》大概是尝试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它,提出了三个层次——政治的理论与主张、理想与口号、情绪或取向,都是为了去解释政治实践。促使我此后不再使用政治文化概念的原因之一,是它天然具有模糊性,容易被随意使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我逐渐意识到,既然我要探寻的是政治实践的原则,那么我其实完全可以不使用这一概念,直奔“原则”而去就好了,方法论在研究中的作用没有我以前想得那么重要。所以在《宋王朝》中,我基本就将关注重心放在了政治思想、理论上,给了道学比较重要的位置。
澎湃新闻:《北宋》主要讨论的是北宋“晚期”,《宋王朝》主要探察的是南宋“后期”。王朝的后半段似乎确实更容易出现历史的症候。对于王朝早期的历史,学界的研究往往更多更细,除去这方面的因素,您将历史的解剖刀插入症状频出的王朝后期,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另外,也许部分读者会有这样的疑问:单单考察南宋后期,能揭示整个宋王朝的形态吗?请谈谈您的看法。
方诚峰:关注两宋晚期确实有基于学术史的考虑——两宋前期的研究相对都比较丰富。此外还有具体原因,在北宋是王安石变法,在南宋是道学的兴起。“数十百事交举并作”的王安石变法极大地改变了宋代政治、社会、思想的面貌,是宋史的枢纽之一。在《北宋》中我关心的就是变法之后政治上的论争、结构、后续实践等等。南宋外则持续面临边防压力,13世纪初金衰蒙兴后更甚。在内,南宋中期道学兴起是一大变数,道学提出了一套自为己至平天下的系统思想,大概此后的中国思想史再也没有如此建树了。南宋后期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就比较契合我感兴趣的问题——原则与实践之关系。还有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原因是,历史中的悲剧成分更加吸引我一点点。
仅仅考察南宋后期,肯定是不能揭示整个宋王朝形态的。如果需要对这种操作进行辩护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句话。两宋各有一些问题贯穿始终,但后期比前期无论就局势还是史料来说都复杂得多,可谓“人体”?当然接下来不能说别人研究的都是猴体。此外,我比较喜欢对历史问题作结构化的理解,或许这样也稍可弥补以偏概全的问题。比如《宋王朝》上篇所谈及的“双重委托”,虽然我用它概括南宋后期政治结构,但“委托”这一基础性概念又是基于我对唐宋政治史、制度史材料的理解。所以,我可能永远无法在具体研究上覆盖整个宋朝,但期待某些提炼可以跨越具体研究。我不是说宋理宗等人的作为都是为了践行所谓结构赋予他们的使命,我只是深信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历史人物确实总有选择,但却是有限度的,也因此我们可以探寻到某些模式。
澎湃新闻:《北宋》和《宋王朝》都对“以今格古”有犀利的批判,前者批判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将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后者批判今人将古代王朝视为低配版的现代国家。《宋王朝》上篇主张宰相是家产制支配的工具,也代表了身份团体、合议制与君主相抗衡,但同时强调此处的“宰相”并非“官僚制”的一部分。官僚制下对君权的抗衡,和家产制下对君主的抗衡,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能否做一个更通俗、更具体的阐述?
方诚峰:我们今天对“官僚制”的认识有时候会有摇摆。单纯讲概念的时候,都很清楚、也很认同韦伯说的官僚制所具有的非人格化的、即事化的目的为导向的特点,各部门有依据规则而来的明确权限,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基本就不存在宰相抗衡君主的问题,因为权限基本是确定的。但我们在研究中使用官僚制概念的时候,常常是,只要看着是个有等级、有分工的行政体系就可以,于是会出现“历史官僚制/历史官僚帝国”这样的说法。这种应用,似乎是取用了官僚制的形式,而丢弃了其精神原则。我们平常说宰相是官僚制的一部分,大概就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说的——宰相确实是王朝制度中的“百官之首”。
但如果加上所谓家产制的精神或专制的精神,那么对于宰相角色的理解就要稍微复杂一些。中国古代君主、宰相的权限与关系,不是根据规则来的,舒卷在我的是君主。一方面,君主对宰相在内的百官每个人有无上权力,这是一种类似于家内主人对家仆、家奴的人身性权力;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权力性质问题,不是大小问题(权力实际也不可测度)。另一方面,由于能力、技术条件、利益、传统等等,皇帝对于官僚队伍整体又是相当无奈的,不得不依赖之,甚至被蒙蔽也无可奈何;我们常说宰相“抗衡”君主,我觉得基本是在这个无奈的意义上才成立。
《宋王朝》在讨论君主支配的时候,与其说是批评以今格古,不如说是批评对中国古代君主、宰相、君臣关系的形式化理解。我强调的是君主对每个宰相、官员无上权力的一面,枢机制也好、委托制也好,简而言之,君主都是主人,而不是官僚制意义中的上级。历史研究中有太多形式主义的理解,看到律令就是法治,看到奏对议论就是民主与公共空间,看到承担赋役的百姓就是纳税人,看到不用术数就是理性科学,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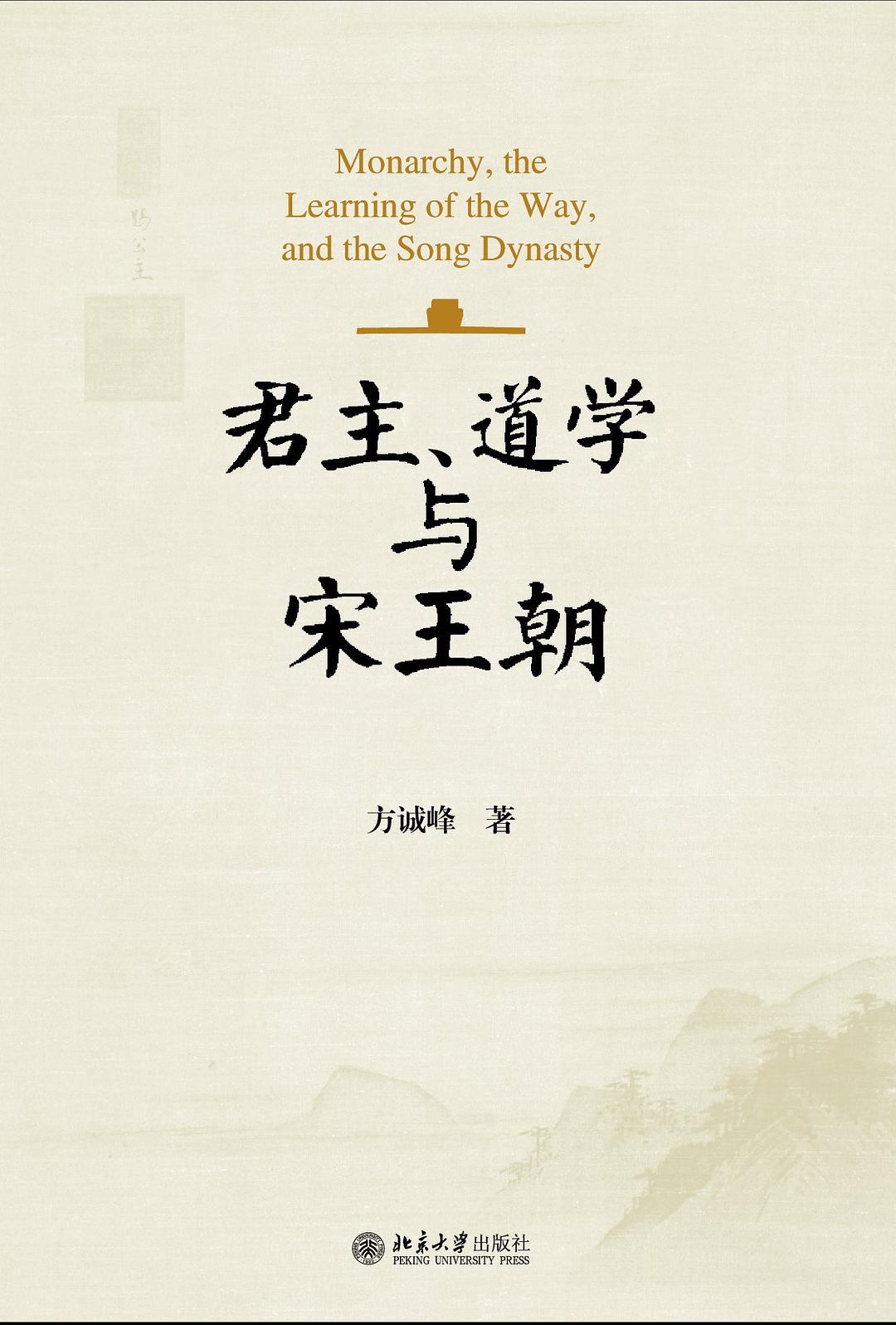
《君主、道学与宋王朝》书封
澎湃新闻:《宋王朝》认为,相较于枢机制,儒家士大夫更倾向于委托制,因此呼吁权相回归(103页)。委托制更符合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现实利益吗?
方诚峰:哪个更有现实利益很难讲,枢机制可以兼容士大夫,但委托制更符合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吧。于士大夫而言,“委任责成”掩盖了君臣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一面,被委任的那个人也与我同类。
澎湃新闻:《宋王朝》下篇主张道学的政治理论分为两截,一截是“明明德”,要求君主做到“先觉”,即君主在政治上成为表率,然而宋理宗通过不断“更化”应对各种“天变”,回应士大夫的批评,而这并不能归为“士大夫政治”那一套,相反宋理宗是在运用当时流行的道学话语,将自己塑造成不断格物致知、格物以明明德的君主。从现实状况出发,似乎很难说道学的“明明德”在君主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也很难定义为失败,不过当时的政治确实陷入了一种泥淖状态。也就是说,所谓“明明德”最终沦为摆架子、无成效的政治仪式。这样理解对吗?另外,欧阳守道认为南宋的困局不在“明明德”这一截(198页),您的意见如何?
方诚峰:君主“明明德”是不是在该词原本的意义上成功了?我想答案一定是:不是。欧阳守道的言论是为了突出自己的重点。确实,就君主“明明德”而言,很难定义是成功,也很难定义为失败。站在宋人的立场,就理宗接受了这套话语、在其逻辑下行动而言是成功的,正如欧阳守道说的,自古以来也没有像宋理宗那样能“讲明性学”的君主。但是,就宋理宗“讲明性学”是否解决了南宋面临的挑战而言,仍是失败。
那“明明德”在君主身上是不是沦为摆架子、无成效的政治仪式?我也不这么认为。我在谈宋理宗“敬天”时,确实突出的是理宗对道学术语的使用乃至利用,使得“居敬穷理”看起来是要求,实际是一种自我论证,是“现实”。但在讲到史嵩之退场的时候,我提到了宋理宗对天变的“五忧”,最终他停止起复史嵩之,正是接受了“克去己私,复还天理”的逻辑。也就是这套话语本身也限制了他的行动。我想没有哪种普遍性的话语会是纯粹空架子。
澎湃新闻:至于道学的另一截,《宋王朝》认为“新民”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行动逻辑,强调南宋末年的公田法(没收豪强之私田,转为公田,以公田租代和籴)是道学家在道学思想指导下,为解决“四海困穷”而作出的努力。然而,推行公田法的道学家却扮演了酷吏的角色,其实际言行甚为苛刻。道学本意是要解决民众在财用上的问题,打造一种伦理共同体,结果却谈不上“恤民”。就此而言,道学“新民”的成效委实有限。您认为“新民”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方诚峰:“新民”指自明其德后推己及人,最终让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即恢复他们原初的理想人格。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条目都属于新民之事。为了实现齐、治、平,尤其治、平,既须垂范教化,又须省赋恤民,使民能各得其所。在南宋,阻碍恤民的因素看起来有二,一是战争,二是豪民。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导致恤民难以真正落实,豪民转嫁负担、把持乡里导致种种赋役不公与残酷压迫。不过战争很难说是根本原因,一来没有战争的时代恤民似乎也没有成功的,二来若无战争的推动,公田法这种击豪强、破兼并的激烈手段似也不会推出。道学家正是在打击豪强的时候表现为酷吏,并非治民皆行刻政。而所谓豪民在宋代主要是官户、吏户,统称形势户,意为有权势之家,甚至道学官僚也是其中的成员。所以,恤民的困境归根结底就在于王朝统治本身,不但赋役刻剥来自朝廷,而且豪民也是王朝体制的产物。但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统治、没有刻剥之法的世界,所以其实我也没有答案。
澎湃新闻: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王安石新学和程朱道学的性质决定(如果“决定”一词过重,或可改为较为模糊的“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在您看来,都曾充当宋王朝正统思想的王安石新学和程朱道学究竟有何不同?
方诚峰:稳妥讲,历史是合力的结果,所以谈不上“决定”。当然,我还是乐于被这样“误解”,因为思想史理应得到更多重视。我们都很熟悉陈寅恪先生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易把他讲的“文化”泛化,而实际他主要是指秦以后中国思想史的“一大事因缘”——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固然“造极”“一大事因缘”的讲法人所熟知,但宋史研究的现实却是相当忽视思想史的意义。虽然不能说新学、道学决定了两宋历史进程,但若不理解其学的“三观”,又何以理解人们的作为呢?
说及新学和道学的差异,因新学未曾达到道学那样的体系性,目前的研究也不充分,我对双方的了解也不够,故不容易比较。据说,程颢曾对王安石说:“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大程以塔刹之相轮喻道,说自己入塔攀登,最终得至塔顶,坐于相轮之中,而王安石却一直在塔外谈论那个远远地高居塔顶的相轮。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王安石所谈的是在我之外的一个“道”,而自己所讲的道终究不离乎己,所以程颢接着评价王安石之学:“只他说道时,已与道离。”
如果就此推论,王安石所阐释的是一种在人之外的道/理,他说:“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致一论》)“精其理”可以简单理解为掌握万物之理,而“星历之数、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学圣人者之所建也”(《礼乐论》)。逻辑上是先有一个外在的道/理,人须掌握此理,然后据以创法立制。相比之下,道学特别强调道/理作为宇宙的普遍法则,“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人性作为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天地间公共之理”是统一的。在这种统一性的基础之上,道学强调道不离乎日用之间,把为己之学摆在了最根本的位置。如《宋王朝》中所言,道学终极的“天下平”理想,指的是事亲、事长这些日用伦常得以普遍实现的状态。必须承认,我这就是吸收学界已有的认识作一个漫话式的比较,以说明双方在人与道/理关系这个基本点上的分歧。出发点既不同,则在实践层面,北宋后期的变法与南宋道学的“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差异也就大了。
澎湃新闻:《宋王朝》的上篇是从专制论、家产制国家论的角度检讨宋王朝君主支配的性质,下篇的道学则要求建立先觉后觉的伦理体系,而非支配与服从的支配体系。也就是说,君主支配与道学追求似乎存在着绝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君主支配的体系下,在坚固的现实、深刻的危机面前,道学遭遇了重重挫折。书中结语认为道学思想是阻碍宋朝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因素,可是宋王朝(及此后的王朝)却选择与道学合作,这又是什么缘故?
方诚峰:这个矛盾可能也没那么大。在逻辑上,道学的“先觉”之人本身就应具君师之位,这正是配合君主支配的。所谓矛盾可能存在于实践中,道学的明明德与新民两截在理论上是自洽的,但一套自洽的理论在不同层次、领域的实践后果是不一样的,这是小书中具体谈的,不赘述。我们现代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
至于道学为何成为帝制中国晚期的正统思想,学界已有的解释我认为是可以采用的。就社会层面而言,科举社会的现实是,仅有少数人才能登科入仕,其余广大士子在仕途之外的种种选择就需要一种有力的论证——如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万理皆一理”,那么只要遵循道学的教诲,日常所行就是在格物穷理,即是修身,即是在履行一个士的政治与社会责任。这样的话,道学受到科举社会的欢迎就可以理解了。通俗讲,道学类似于告诉大家,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光荣。就政治层面而言,再也没有比道学更好地论述君主君师合一角色的学说了,而且实践起来也不像理论看起来那么繁琐,君主们自是十分乐意采信。在明清史中,君主的君师合一角色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在宋史中,因为经自由主义解读的“士大夫政治”概念的流行,皇帝作为道统传承者的事实被选择性忽视了。总的来说,道学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提供了最为完备的正当性论证,从而成为帝制中国晚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