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光从音乐厅的穹顶打在舞台中央,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从光中显现出来,犹如茫茫大海上一条发亮的渔船,孤独飘零。拉法尔·布雷查兹还没有上台。等待演出开场的时刻总是令人兴奋,像等待一场酝酿已久的大雨,此时上海的这场大雨倒也连绵下了两天之久。水涨船高,三角钢琴静默着,露出黑白相错的犬齿。你一定看得出,桀骜不驯只是表象,这条自主沉浮的渔船正等候它的船长,它渴望被演奏家灵巧的双手驯服。

语言是无可奈何妥协之物。人类发明语言,用以对事物进行定义和归类,然而深层大意往往是天上飘忽不定的星云。在西方神的叙事中,人们竭尽一生修建通天的巴别塔,是盼望有天能彻底打破言与言之间的铁幕,可事实证明,这大概是徒劳。东方人则早早顿悟,于是仓颉取象造字,“象”是地上的草、水边的鸟、手边的火,一个字就是一幅图画,诗人低吟:“言有尽而意无穷。”语言只是指向月亮的手指,你要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到月光,而不是将目光困囿于手指的牢笼。
拉法尔·布雷查兹在众人的注目下径直走上台,他长得苍白、俊美、干净,这是他的首次来华演出,参加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作为2005年第1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同时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囊括波兰舞曲、玛祖卡舞曲、协奏曲等所有乐曲种类最佳演绎奖的大满贯得主,亦代表主办国波兰在30年后重夺此项赛事的冠军,有些古典乐迷们充满爱意地认为,他长得酷似肖邦。怎么会不像呢?他有着一头蜷曲的头发,眼睛深邃而迷人,总是面带笑意,手指纤长,传言肖邦独特的“肖邦弹奏法”正源于肖邦本人消瘦的身材和强劲的骨骼。一切好似轮回。

布雷查兹坐下,燕尾服的燕尾垂在椅后,他在钢琴前沉寂片刻——在过往的现场演出中,他常常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手帕,轻柔而迅速地拂过面前的钢琴键盘,像用羽毛拂过爱人的面颊。这似乎成为了他的标志性动作,好比古尔德弹琴时总要把头低得快要贴近键盘,一边演奏一边小声哼哼。实际上琴键上并无什么灰尘,进入魔法前的瞬间是紧张的,音乐家总要在演奏前凝神静气,通过惯性动作来创造自己的空间。
如果言语终究徒劳,请想象一个仅由音乐语法构成的世界,五线谱阡陌交通,音符和音符如雨滴般参差跌落,高音部和低音部的并行犹如溪水流过浅滩、礁石,附点是午后的阳光穿透森林,光斑随着太阳的移动而蜿蜒逶迤。二分音符的长吁搭配十六分音符的短叹,休止符在喧嚣中留出空白,真诚的缄默可以在此发生。
洁癖代表着一种内省和自控,布雷查兹是技术的洁癖者,能够突围标准严苛的肖赛,并将所有单项奖项都收入囊中,这意味着背后长时间的规律练习和对技术的艰苦打磨,技术的精巧犹如一面丝滑而平整的玻璃,能吸纳来自不同角度的光,但却容易由此牺牲锋芒和锐利。“全面”,某种意义上也在暗中产生个性的磨损。

第一首贝多芬的《升c小调第14号钢琴奏鸣曲“月光”》,越是耳熟能详的曲子越难弹,因为越容易滑向套路而流俗。演奏家一方面为了突破自我,要跟陈词滥调做斗争,另一方面古典音乐界心照不宣的“忠于原作”的刻板规则,让演奏家潜意识里为了维持演出的平均效果而趋于保守,分寸感体现演奏家技术的细腻,曲目的选择是市场需求和自我表达间小心翼翼的辗转拿捏。“自我”,在密不透风的技术藩篱中会时不时地跳将出来,在正楷端正的字帖上留下一笔苍劲的草书。
萨义德认为贝多芬是一个彻底世俗的人,代表着饱满又充沛的酒神精神,“以顽强、近乎创业者英勇无畏的精神终究赢得了成功”,如果说每一位艺术家都有其特殊的调调,“对于贝多芬,这种调调则是简单的旋律与坚持不懈、时而充满爆炸性的发展序列之间的紧张感”。
然而《月光》在激昂中是带有柔情的,柔情蜜意是硬汉跪在岸边掬起一汪溪水,是猛虎细嗅蔷薇,是战斗中的骑士不忘轻手托起从鸟巢中坠落的雏鸟,李斯特将第二乐章形容为“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花”。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在布雷查兹的演绎下,月光从第一乐章的低沉朦胧、幽微神秘,随着云影的漂浮移步换景,时而显露出生命的残暴和退居一隅的哲思。转而第二乐章的甜美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月光开始变得调皮起来,甚至狡黠地在云影间来回闪躲,这种嬉戏的透明质感不留痕迹地过渡到了第三乐章,青年式的激昂在此处爆发——鲁宾斯坦处理这一章节时,习惯于用层次分明的强弱制造一种愤怒的轻盈感,布雷查兹则与其不同,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他就将乐章的调子拉到一个紧张的高度,像绷在弓弦上的箭。右手一连串的琶音快速而清晰地飞过,一浪高过一浪,每个音都掷地有声,生命的鼓点犹如盘旋在悬崖上空的飞鹰,在不断酝酿爆发的激情中时刻保持警觉。

下半场的肖邦是布雷查兹的演奏舒适区,《三首玛祖卡舞曲》和《b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其演奏也渐入佳境。笔者以为,肖邦的抒情是极具东方式的,正如哈聂卡对肖邦夜曲的评价:“肖邦所努力的不是单纯的表达,而是经过装饰,太过于阴郁、热带性,或说带有东方的气息。”
肖邦抒情性的诗意,源自一种被高度管理和调制的情感配方,通过“丰富的细节装饰和对位细节”,将过分溢出的情感转化为一种萨义德所言的“凌厉的专注”,这就好比中国的传统诗歌,奔涌而出的情感经由平仄韵律的过滤,最终呈现出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适度情感。
罗森在《浪漫一代》中写道:“在肖邦感性的表面底下,藏着规划、复音、和声创意上的纪律……肖邦风格的核心是一种悖论,是一种表面看来不能实现的结合:那是他基于对巴赫深刻的体验,以半音形成丰富的复音网络,加上直接从意大利歌剧衍生而来的旋律意识,以及支撑旋律线的方式。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这矛盾浮现出来,你也能感觉到这其中的吊诡。这两股影响在肖邦手里得以完美结合,并且互相赋予对方新的力量。”
笔者以为,演奏肖邦的关键在于一种精细的控制,即“他毫不留情,要求钢琴家弹出那种几乎矛盾、无法实现的细腻兼暴烈”,也就是说,演奏家必须懂得拉紧缰绳,去制服性情暴躁而多愁善感的烈马,又不能伤及其扩张的生命力;从悬崖上一跃而下,又轻盈自控如一根光洁闪亮的孔雀羽毛。

因此从情感文化脉络上来看,中国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肖邦。傅聪演奏的肖邦夜曲,就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朴拙的古意,像是隐士于山林中练剑,那种洒脱自在的气质如中国山水画般泼墨写意,而非精雕细琢的工笔写实。
激情的张力在于控制,如果没有绝对的冷静,就无法拥有绝对的激情。《b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在布雷查兹的演奏下,由四个动机构成的乐句,以庄严肃穆的气质倾泻而出,继而动机不断重复,调子比第一次略显晦暗,显出一种迫切的心情,随着左手雄厚低音的进入,庄重感和戏剧性不断增强,苦闷的情绪作为一种被压抑的底色,在旋律的起伏中时隐时现。
当第二主题呈现时,旋律顿时变得清丽婉转起来,仿佛拨开了重重迷雾,音色透明的质地像是被清晨阳光包裹住的露珠,从薄如羽翼的花瓣一路滑向花蕊深处。然而激昂和暴烈仍然如影随形,并行于如歌旋律的底色,构成一种情绪上复杂的重影。
进入第二乐章,这种激情蜕变为一种轻快而流动的诙谐,斑斓的色彩让人眼花缭乱。转而进入第三乐章,色彩又开始变得纯净,如同江面上的烟霞、山林中的薄雾、珍珠上的波纹、湖水中氤氲的花影——安宁只是暂时的,第四乐章用连续几个强有力的和弦在湖面上掀起波澜,湖水瞬间被搅浑,持续扩大的涟漪带来了波动的紧张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左手华丽的上行犹如咆哮,在回旋曲的进行中有一种跌跌撞撞的不和谐感。情绪在不断的叠加攀升中最终达到高潮,“世界以痛吻我,我将报之以歌”。

当最后一个音符的终止式落下,整个音乐厅重新归于安和静,演奏家和三角钢琴同时坐在穹顶的光芒里,上一秒音乐的幻影依稀可见,那个因言语的缺席而由音乐构建起的世界瞬间落幕。此时,音乐止处,语言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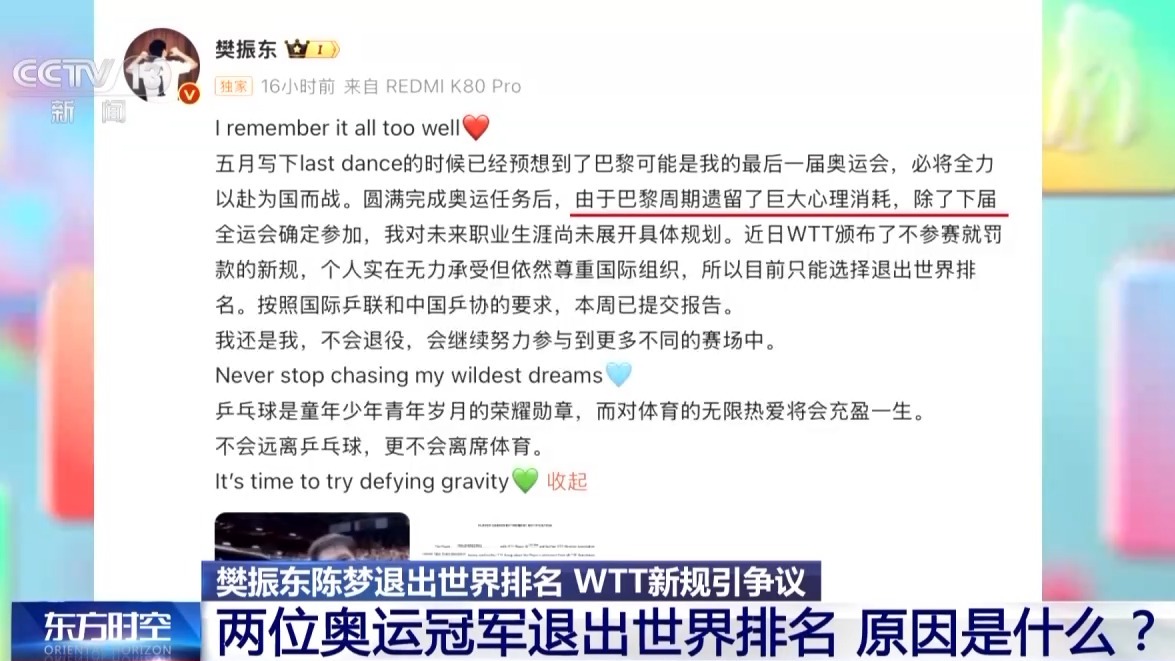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