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狐工商代办(电/微:17379593519)安义县有县公司营业执照注销流程和费用,电商执照代办 个体 个独 公司 食品证许可证 出版物 二类医疗 ICP许可证各类营业执照,记账报税 年审年报 清税证明 注册注销业务 一切疑难问题,都可以咨询拒绝一切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报送相关部门!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安义县有县公司营业执照注销流程和费用,以及安义到哪办营业执照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微信号:MD80086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本文目录一览:
在安义县自己开店的有营业执照,自己只交职工医保不交社保可以吗?_百度...
1、自己有营业执照,可以申请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社保,你可以选择只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的待遇基本上是一样的。
安义县有县公司营业执照注销流程和费用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安义到哪办营业执照、安义县有县公司营业执照注销流程和费用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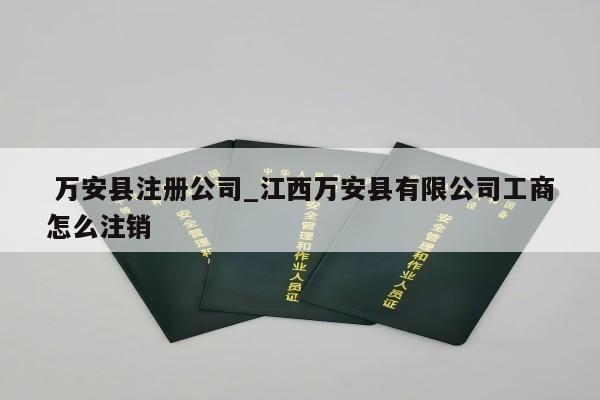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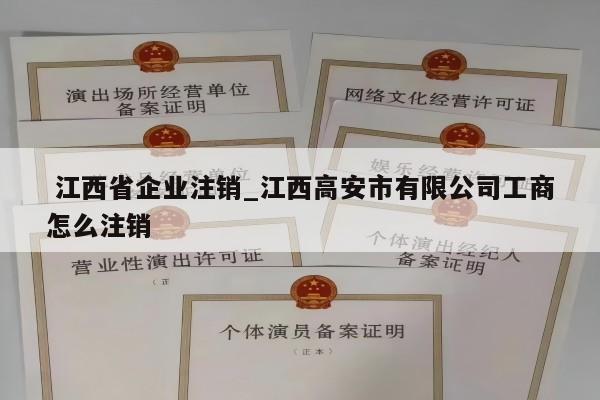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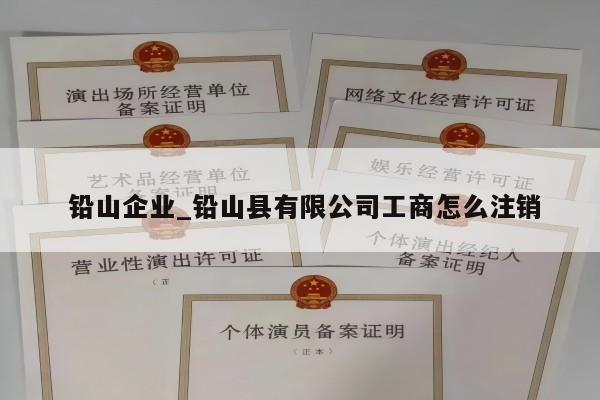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